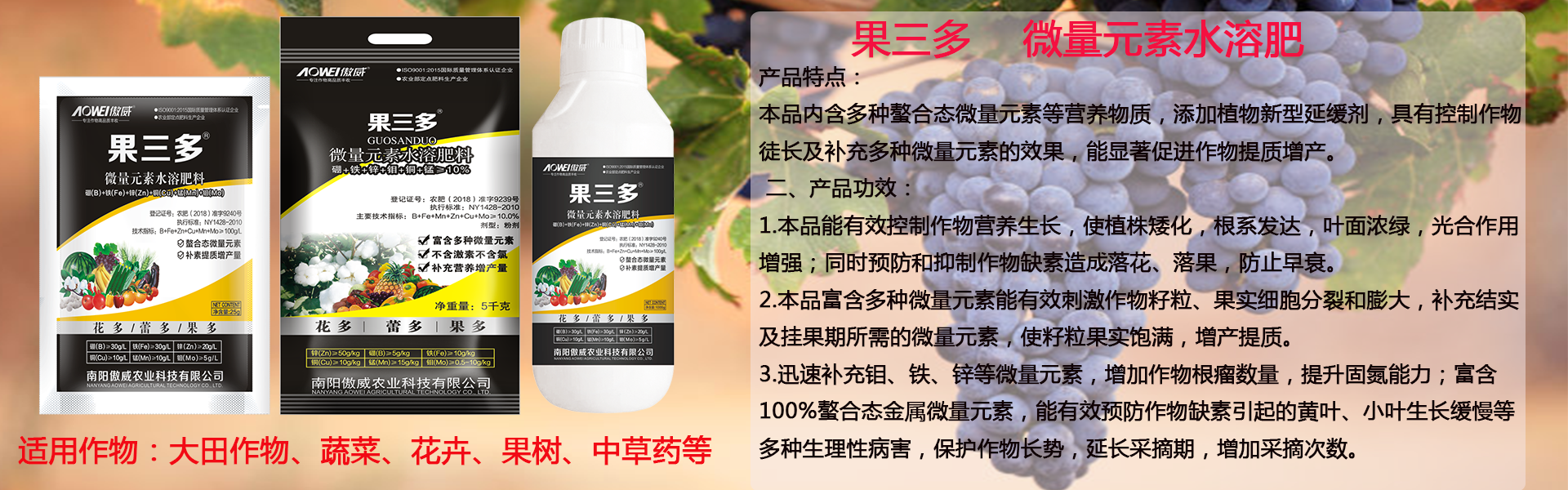九游会总部:范志勇:历史上的美国贸易政策(十一):19世纪90年代的“互惠运动”和对等关税的初步实践
来源:九游会总部 发布时间:2025-09-13 06:26:45
-
ag九游会登陆入口:
范志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书记、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2025年的8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全世界开出了一份“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清单,对不同国家征收不同的税率。此前,特朗普在7月7日时曾表示将对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于违逆美国意志,执意要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印度,则决定征收50%的对等关税。
如果您一直关注本系列文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从美国建国开始征收关税起,一直是对特定的商品征收特定的关税,而不关心这个商品的原产地。当然战争等特殊情形除外。例如,美国政府决定对羊毛征收50%的关税,那么所有进口到美国的羊毛都会被征收该税率,而不管羊毛到底是英国生产的,还是澳大利亚出产的。
这似乎和美国现代关税体系有显著的区别。那么美国是从何时开始,对不同国家开始实行差异化的关税税率呢?这是这一节我们将要介绍的内容。
除此之外,2025年美国开出的关税被称为“对等”(Reciprocal)关税。那么这个对等关税是啥意思?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国家层面的“对等关税”,例如,如果某国对美国商品征收100%的进口关税,美国也将对该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商品层面的“对等关税”,例如,目前美国对来自某国的某种商品征收2.5%关税,但对方对来自美国的同种商品征收10%关税。一旦实施“对等关税”,美国将把进口自这一国的这种商品关税提高到10%。以及非关税壁垒层面的“对等关税”等等。美国单方面称,征收“对等关税”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解决与贸易伙伴之间“其他不公平和不平衡的贸易问题”。贸易伙伴的关税税率、行业补贴、税收政策等,都是用来评估“对等关税”税率的因素。
英文reciprocal一词在中文中既可译为“互惠”,也可译为“对等”。以往贸易机制安排中,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前,中文译法多为“互惠”,体现贸易“伙伴”互利共赢的精神。根据标准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和美国可以分别在中低端和高端产业实现分工并通过贸易改善两国人民的整体福利。然而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一面对中国一直在升级贸易战,一面声称关税要“reciprocal”。此时中国人才慢慢地认识到,原来美国人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没有“互惠”的意思,而是强调“对等”的含义。自此之后,原来的“互惠关税”在中文语境中被重新翻译为“对等关税”。
Reciprocal Tariff 无论是称为“互惠关税”还是“对等关税”,都不是特朗普新发明的产物。其源头是19世纪末逐渐兴起的一场“互惠运动“。这场运动深刻的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关税政策。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生产能力的提升,关税政策出现重大转型,从保护国内市场转向开拓国际市场;通过与拉丁美洲国家互相减免和降低关税,美国慢慢地增加和巩固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在事实上不断强化”门罗主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税减让还真体现出互惠的性质。因此在下文中,我们仍旧是把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称为”互惠运动“。
从经济发展背景来看,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商品出口已超越进口,迎来了持续的贸易顺差。此时距离南北战争结束仅仅十年。然而这一时期整体贸易顺差的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从1880年到1895年年均商品贸易顺差约在9千万美元左右。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对外出口迎来快速的提升。从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年均贸易顺差达到4.5亿美元。
一方面出口量迅猛增长。按名义价值计算,1895年出口为8亿美元,1914年达到23.6亿美元,年均增长6%左右。另一方面,出口结构一直在优化。在1890年至1910年间,美国彻底颠覆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模式。制成品出口量急剧上升,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从1900年的35%直线年,出口制成品的价值翻了一番,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从26%攀升至35%。在这5年中,制成品的出口量令人咂舌地增长了90%。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生产迅猛增长。1870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中的比重为23%。到1913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中的比重达到36%。出口的迅速增加改变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美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从1890年的4%攀升至1913年的11%,随后在1929年达到18%。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制成品产量以及出口量中的占比快速上升,但是制成品出口量在美国制成品产量中的比例相比来说较低,且保持稳定。例如,在1914年美国制成品出口在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约为6%,与1879年的比重基本持平。在除石油、化学制品和加工食品等之外的绝大多数产业里,出口在国内产量中的比重从来就没超过10%。[2]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美国在工业化速度远超于当时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工业品大多数都用在不断深化国内的工业化水平。
在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是否依然有必要利用较高的保护性关税限制进口;相反,能否利用关税工具帮助美国出口打开外国市场成为这一时期人们考虑的主体问题。由此产生了互惠的观点,为贸易政策另辟蹊径。
尽管在美国更早期的关税实践中也有一些“互惠”的行为,但是19世纪末的这场“互惠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共和党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1830-1893)。他曾经两次出任众议院议长和国务卿。布莱恩主张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互惠关税协定”,削减来自这些国家热带地区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不对美国内的生产者构成竞争),而作为交换,这些国家也相应下调对美国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从而为日益扩张的美国制成品产能扩大市场。
布莱恩认为“互惠关税协定”至少会从三个方面给美国带来收益:首先,互惠协定能够扩大制成品出口,又不会将本国产业置于外国竞争中,从而巩固了经济。其次,互惠通过削减部分进口关税平息了对高关税的攻击,巩固了国内对保护性关税的政治支持。这其实就是共和党历史上惯用的“丢卒保车”策略,从亨利・克莱时期就多次采用过。再次,互惠协议会巩固美国与拉美地区的关系,有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利益,从而使该地区疏离英国及前宗主国。
布莱恩在哈里森政府担任国务卿后,从1890年开始继续推动美国加强与拉美国家的联系。他坚持在《麦金莱关税法案》(1890年)加入互惠条款,赋予行政部门与其他几个国家磋商贸易协定的权力,使后者降低美国出口进入外国市场时遇到的障碍,以换取这些国家的非竞争产品在进入美国获得相应的关税减让。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允许总统在某些国家对美国出口征收“不平等或不合理”的关税时,暂停该国产品进入美国时享受的进口免税待遇。由这样来看,《麦金莱关税法案》体现的是惩罚性互惠,即美国没有对其他几个国家提供关税减让,而是要求其他几个国家为美国出口提供优惠待遇,否则就威胁对它们的进口施以处罚并征收报复性关税。
在1891年至1892年间,布莱恩签署了十份互惠协定。在这些外交实践中,巴西取消了对美国小麦、面粉、猪肉和农用设备的关税,还调低了其他美国产品的进口税率,这样巴西出口到美国的兽皮、糖和咖啡就能够继续免税进入美国。相反,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海地未能做出让美国满意的回应,因此被征收了惩罚性关税。美国关税委员会(US Tariff Commission,1919,第28页)后来总结,《麦金莱关税法案》中的这一条款“无论是作为报复手段,还是确保美国享受优惠关税的手段,都适度有效”。
互惠运动并非一帆风顺。认为互惠条款并没有真正起到全面降低进口关税的作用,只是针对那些与本国生产者没有竞争关系的商品采取了关税减让。因此在1892年大选获胜后,于1894年《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终结了最初的“互惠运动实践”,重新对食糖开征统一关税,布莱恩的互惠贸易计划就此告终。美国政策反复无常,使拉美国家极为愤怒。他们强烈抱怨美国废除互惠协定,因此对美国进口征收更高的关税予以报复。
1893年至1896年的经济衰退为“互惠关税”运动创造了新机会。经济萧条期间人们迫切希望美国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摆脱经济萧条,这使得关税政策辩论的重心从利用高关税抑制进口转向扩大出口的海外市场。1895年后制成品出口迅速扩张,表明外国消费者有潜力成为美国产品重要的需求来源,只要生产者能够进入这些外国市场。
与此同时,进入19世纪90年代之后,各国歧视性关税政策实践愈加明显。在此期间,德国签署了多份包括关税减让内容的双边贸易协定,但美国均被排除在外。1892年法国推出梅里纳关税(Meline tariff),制定了包括最高和最低两种税率的双层进口关税税则;由于美国和法国未签署互惠贸易协定,所以美国产品需按最高关税征税。大英帝国的附属国也开始互相给予优惠待遇。1897年加拿大为英国产品提供了为期三年,税率为25%的关税优惠。到期后关税上升到33%。总体看,19世纪末期,西方主要列强与其殖民地之间构成的贸易网络不断扩张,而且变得愈发排外。[3]
因此尽管共和党在整体上仍认可高关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但也逐渐接受“互惠关税”可能带来的效果。例如麦金莱在竞选时表示只要不放弃为国内产业提供贸易保护的做法,就会拥护“互惠关税”的主张,“我们大家都希望达成的互惠贸易能给我国剩余产品打开外国市场,相应地对那些我们不生产的外来产品开放本国市场。”[4]
在1897年通过的《丁利关税法案》中,共和党再次尝试推行互惠贸易。对于为美国商品提供“互惠和平等关税减让”的国家,该法案首次赋予总统削减进口关税的权力,即对于平等地给予美国关税减让待遇的国家,总统可以对有限数量的产品(即“这些国家出产,且美国没有的天然产品”)下调关税(关税削减措施的效力不超过两年,削减幅度不超过20%,且相关协定的有效期不超过5年)。此外,该法案还再次引入《麦金莱关税法案》中的惩罚性关税条款,赋予总统酌情决定权,即对于任何被美国认定为“在互惠方面采用不平等、不合理”的贸易政策的国家,总统有权取消对其部分进口商品免税的待遇。
图2显示尽管《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案》作为一部典型的共和党保护性关税法案明显提升了应税商品的税率,从1890年的44.7%上升到1894年的50.4%,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5]但在这部法案生效之后,全部商品的关税税率确显著下降。整体关税税率从1890年的29.6%下降到1894年的20.6%,整整下降了9个百分点。根据对整体关税税率的分解,很容易发现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应税商品在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下降造成。不难发现,提高关税使得免税商品对应税商品产生了相对的替代影响。粗略计算,整体关税税率下降了30.4%(9%/29.6%),应税商品关税税率下降11.3%(5.7%/50.4%),应税商品占比在关税法案实施前后变化了19.1%。作为体现降低关税主张的《1894年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虽然废除了“互惠贸易”条款,却实现了应税商品税率的一下子就下降。应税商品税率从1894年的50.4%下降到1896年的40.2%,但是在此期间,整体关税税率基本保持稳定。《1897年丁利关税法案》实施之后,应税商品税率和整体关税税率分别提升了10个百分点和7.6个百分点。

1897年10月,麦金莱总统任命前国会议员兼资深外交官约翰·卡森(John Kasson)率领国务院特设的一个互惠贸易部门,专门负责互惠协定谈判。美国政府依据《丁利关税法案》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士等欧洲国家签署了“互惠贸易协议”。依据这一些协议,德国取消了对美国肉类出口的限制,并对绝大多数美国产品征收协定关税。其后,卡森依据《丁利关税法案》赋予的更广泛权力,与11个国家签署了互惠协定(这些国家大多分布在在中美洲地区)。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协议由于缺少总统和国会的支持基本没有转化为线年随着麦金莱遇刺身亡。美国对互惠政策的兴趣昙花一现后便迅速湮灭,两党的贸易政策主张依然僵持不下。美国再次谈及互惠关税需要再次等待20年时间。

应税商品税率与应税商品占比并不必然是负相关关系,因为在每次关税改革过程中,国会都可能改变应税商品目录。